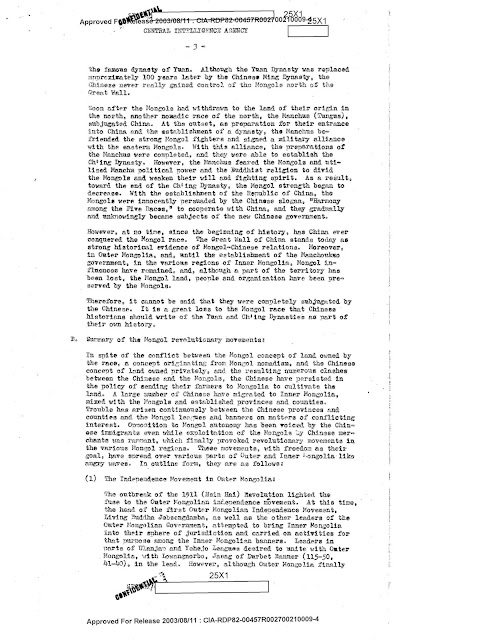2017年1月30日星期一
珍稀野生物种塞加羚羊近期在蒙古国境内大规模死亡
据联合国新闻处消息,珍稀野生物种塞加羚羊近期在蒙古国境内大规模死亡,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消除危害野生动物的疾病的关注。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正在与多国一同努力,以期到2030年根除对野生动物造成破坏性影响的瘟疫。
近期,大约900只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 mongolica) 在蒙古国的西霍省(Khovd)死亡,占该亚种群的近10%。采集的样品显示,这些羚羊对"小型反刍动物瘟疫"(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呈阳性反应。这种瘟疫是对家畜绵羊和山羊具有高致死性的病毒性疾病,导致高达90%的感染该病毒的动物死亡。
小型反刍动物瘟疫在20世纪40年代首次在科特迪瓦被发现,现在已经蔓延至75个国家。据统计,在全球约21亿小型反刍动物中,80%分布在受该瘟疫影响的地区。 粮农组织首席兽医官员鲁布罗特(Juan Lubroth)表示,尽管野生动物一直被认为是脆弱的,但是在野生山羊物种中,感染该瘟疫的实际病例很少,在野生羚羊中甚至从未被记录过。
这次大规模死亡事件极有可能是被感染瘟疫的家禽传染,特别是在冬天,觅食范围较少,野生羚羊与家禽只能分享同一个牧区。
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努力调查实地情况以及可能的其他原因,比如细菌感染。 鲁布罗特说:"我们需要政治意愿、资金、国际合作来消除这一疾病。同时需要加强对家畜的监测和疫苗接种,这是目前可用于保护这一濒危物种的主要工具 。"
蒙古国的赛加羚羊曾经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上,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在秋季,它们为了繁殖和早春产犊进行季节性迁徙。 蒙古国曾在2016年9月首次发生小型反刍动物瘟疫。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当即行动,开展了控制疾病传播的紧急和中期行动。目前,超过1100万蒙古国小型反刍动物已经接种了疫苗。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于2016年启动了小型反刍动物瘟疫全球根除计划(PPR-GEP)以期在2030年彻底根除这种疾病。2017 - 2021年期间为该计划第一阶段,预计花费为9.96亿美元。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
蒙古官员:蒙古经济面临危机
蒙古国外交部外贸经济合作司司长恩赫包勒德先生16日说,蒙古国经济面临危机。 恩赫包勒德先生是当天下午在蒙古国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蒙中投资洽谈会"上做的上述表示。
"蒙中投资洽谈会"是由蒙古驻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广东茂名乙烯集团联合举办的。蒙古国政府有关部门官员、中国企业家代表200余人出席了洽谈会。 恩赫包勒德说,蒙古政府的换届,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的不稳定是造成蒙古经济下滑和面临危机的原因。
蒙古新一届政府已经于2016年组成,其正在做改善蒙古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工作。 他称,在新一届政府执政的4年时间里,蒙古国的投资环境应该是稳定的。政府将吸引投资,启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他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蒙古两大邻国,在蒙古经济发展上起着巨大作用。
三国正在合作建设着的"蒙俄中经济走廊"也会推动三国经济的发展。 在洽谈会会上,蒙古国交通运输发展部的官员介绍了蒙古即将启动的铁路和公路项目情况。中国广东茂名乙烯集团董事长黄志先生介绍了向蒙古国投资建设铁路和公路的情况。
【南蒙古草原風#1】 - 世界南蒙古大呼拉尔 (视频)
"Өмнөд Монголын талын салхи" нэвтрүүлэг бол хятадын коммунист засгийн үндэстнийг уусгах бодлогийн хоморгоонд байгаа Өмнөд Монгол орны бодитой ахуйн байдал, мэдээ мэдээлэл, соёл түүхийг танилцуулахаар гол зорилго болгосон нэвтрүүлэг болно
Хөтлөгч: Олнууд Дайчин (Өмнөд Монголын Их Хуралдайн нарын бичгийн дарга)
Фүрүкава Фүми-Эцү
Анхны дугаартаа"Өмнөд Монголын Их Хуралдай" болон хуралдайн Тайван дахь ажилгааг танйлцуулах болно
【南モンゴル草原の風 #1】世界南モンゴル会議「クリルタイ」/モンゴル音楽「ホーミー」 [桜H29/1/12]-Published on Jan 11, 2017
「南モンゴル草原の風」は、中国共産党により民族浄化の危機にある南モンゴルの現状やニュース・文化・歴史等を多言語でご紹介する番組です。
進行:オルホノド・ダイチン(世界南モンゴル会議幹事長)・古川フミエイツ
第一回は、「クリルタイ・世界南モンゴル会議」結成大会と台湾での活動について報告いたします。
Хөтлөгч: Олнууд Дайчин (Өмнөд Монголын Их Хуралдайн нарын бичгийн дарга)
Фүрүкава Фүми-Эцү
Анхны дугаартаа"Өмнөд Монголын Их Хуралдай" болон хуралдайн Тайван дахь ажилгааг танйлцуулах болно
【南モンゴル草原の風 #1】世界南モンゴル会議「クリルタイ」/モンゴル音楽「ホーミー」 [桜H29/1/12]-Published on Jan 11, 2017
「南モンゴル草原の風」は、中国共産党により民族浄化の危機にある南モンゴルの現状やニュース・文化・歴史等を多言語でご紹介する番組です。
進行:オルホノド・ダイチン(世界南モンゴル会議幹事長)・古川フミエイツ
第一回は、「クリルタイ・世界南モンゴル会議」結成大会と台湾での活動について報告いたします。
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
蒙古国总统说必须严控首都的空气污染
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11日说,首都乌兰巴托的空气污染已达到“灾难”程度,必须采取严格措施控制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
由蒙古国总统、议长和总理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0日召集相关部门举行了首都空气污染问题研讨会,就乌兰巴托市政府提出的应对空气污染举措进行了讨论。
额勒贝格道尔吉11日在首都空气污染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乌兰巴托市政府限制牧区民众迁往首都的政策,乌兰巴托市应该进一步限制对煤炭的使用,禁止燃烧垃圾。
此前,为鼓励棚户区居民减少燃煤取暖,乌兰巴托市政府宣布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夜间免费向棚户区居民供电以解决取暖问题,但当地的空气污染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明显好转。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乌兰巴托北部棚户区的细颗粒物(PM2.5)浓度经常超过1000。
乌兰巴托冬季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40摄氏度,冬季时间超过6个月,取暖期长达8个月。半数以上乌兰巴托市民居住在城市北部的棚户区,那里基本没有集中供暖设施,居民靠在蒙古包或简易房中烧木头和煤炭等取暖,造成整个城市空气中经常弥漫着呛人的味道。
由蒙古国总统、议长和总理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0日召集相关部门举行了首都空气污染问题研讨会,就乌兰巴托市政府提出的应对空气污染举措进行了讨论。
额勒贝格道尔吉11日在首都空气污染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乌兰巴托市政府限制牧区民众迁往首都的政策,乌兰巴托市应该进一步限制对煤炭的使用,禁止燃烧垃圾。
此前,为鼓励棚户区居民减少燃煤取暖,乌兰巴托市政府宣布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夜间免费向棚户区居民供电以解决取暖问题,但当地的空气污染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明显好转。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乌兰巴托北部棚户区的细颗粒物(PM2.5)浓度经常超过1000。
乌兰巴托冬季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40摄氏度,冬季时间超过6个月,取暖期长达8个月。半数以上乌兰巴托市民居住在城市北部的棚户区,那里基本没有集中供暖设施,居民靠在蒙古包或简易房中烧木头和煤炭等取暖,造成整个城市空气中经常弥漫着呛人的味道。
达赖喇嘛受邀为菩提伽耶蒙古国新寺院开光
【西藏之声2017年1月10日报道】蒙古国甘丹大乘寺在印度菩提迦耶新建分寺——巴卡斯坎寺(音译),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前去为该寺开光。在仪式上尊者呼吁蒙古僧侣学成返家后,要为佛法在蒙古的发展而付出努力。
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向聚集的两千多名蒙古国僧俗给予开示,指出西藏与蒙古间有着数千年的深远历史关系,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就出生于蒙古,而且历史上也有许多蒙古大师在西藏各大寺院修学佛法,因此现今的蒙古僧尼众也应该继承先辈的精神,勤学佛法。“今天在座的各位中,有很多年轻的僧侣,你们要多多阅读佛教经典,精进学习。”
尊者提出,目前在印南格鲁传承三大寺中学习的蒙古学员,承担着一个国家佛教事业的传承发展。“目前藏人在流亡中,无法为你们提供非常完善的学习条件,但是我们要同甘共苦,大家在各寺院中应努力学习,学成返回蒙古后为当地佛教事业发展做出努力。同样,蒙古境内的各寺院也要为归国的僧尼众创造机会,让他们有施展所学之地,如向当地信众教授佛法。”
达赖喇嘛尊者也在开光仪式上指出,蒙古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复兴佛法,但仅仅靠修建寺院与佛像并不能复兴佛法,而是应通过闻、思、修,来让佛教思想得以延续。“佛教在于内心的转变,所以学习教典最为重要。”
达赖喇嘛尊者强调,身处21世纪,佛教徒们也要与时俱进,注重学习教典,不能再追从盲目的信仰,不能只将佛教视作习俗,而是应该通过正确地认识佛法,再去加深各自的信仰。
此次由达赖喇嘛尊者开光的巴卡斯坎寺,是设立于印度境内的首座蒙古寺院。目前有约8百名蒙古学员在印南各大藏传佛教寺院中学习佛法。
再论兀良合部落的变迁
二十世纪初,日本蒙古史学者简内亘发表《兀良哈三卫名称考》一文,最先开始探讨兀良合部的渊源。1917年,日本蒙古史学者和田清著《内蒙古部落的起源》一书,论证明代兀良合人是元初游牧于斡难河流域的兀良合人的后裔。可是他在说明清代兀良合人的来源问题时却感到十分为难。
近十多年来,我国有些权威学者曾提出兀良合是古代蒙古高原林木中百姓的"泛称"。1985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族女学者奥登同志发表《蒙古兀良哈部落的变迁》一文,对"泛称论"给予有力的驳斥,并对明代兀良合三卫诸问题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但我觉得,奥登同志对原来森林兀良合、不儿罕山兀良合的论述并不完全使人满意。
在1988年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在《兀良合部落的变迁》一文的提要中我写道:从十三世纪蒙古兴起到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汗国灭亡的五百多年期间,兀良合部发生了多次变迁,每次变迁之后兀良合一名所指的部落也有很大不同。
概括起来讲:
第一、确实从森林兀良合或草原兀良合演变过来并由原真正的兀良合人构成的部落,如绰罗斯、塔崩、鄂尔多斯、额鲁特、小额鲁特、杜尔伯特、喀喇沁、准噶尔等。
第二、因为统治者是兀良合部人而一度被称为兀良合的部落,如蒙古勒津、阿尔泰·兀良罕、唐努·兀良罕等。
第三、由于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或者荣誉的追求而被命名和冒名的兀良合部,如原秃绵·乞儿思吉之各部以及巴尔浑、不里牙惕等。
第四、由于被统治者是兀良合人而统治者自己也称为兀良合部落,如科尔沁等。
论文提要在1988年《内蒙古师大学报》第三期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不少蒙古史学者的兴趣。蒙古国科学院纳楚克·道尔吉院士认为,在提要中提出的论点确实很重要,希望早日写出全文。日本一位教授表明,提要中的某些论点他曾提出过。香港有位学者认为,近几年我发表的有些文章解决了明代蒙古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
1989年八月初,在内蒙古大学由中国蒙古史学会主持召开的明代蒙古史专题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蔡家艺同志说,在提要中提出的有关兀良合的论点确实值得研究,因为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卫拉特各鄂托克、昂吉、集赛中,特别是在鄂托克中确实有不少兀良合人。奥登同志认为,近几年我发表的论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某些论点肯定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卫拉特史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同时,部分学者对我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主要有下列三点:第一,蒙古文献不可信,特别是所谓托忒蒙古文献是由于某种政治需要而后人随意伪造的,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第二,兀良合是成吉思汗直辖部落,卫拉特是成吉思汗驸马的所属部落,二者之间根本不同,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第三,如果新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前人长期以来有关卫拉特史的研究成果全盘被否定,蒙古史需要重新写了,等等。在这里,对以上不同意见我不想一一给予答复。趁此机会,关于兀良合部落的变迁问题补充几句。
兀良合是在蒙古各部落中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部落。从十世纪初开始,在辽、金时期的汉籍中曾多次提到兀良合。据《辽史·太祖本纪》记载,十世纪初兀良合部的牧地在辽都临潢府西北,并同辽廷建立了经济关系。在拉施特《史集》中,兀良合被区分为森林兀良合和兀良合两部分,并明确提出兀良合住在巴尔忽真·脱窟木境内。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第十世祖朵奔·蔑儿干时代,豁里·秃马惕部的豁里剌儿台·蔑儿干听说不儿罕山一带便于捕猎,举家投奔了不儿罕山的主人兀良合部的晒赤·伯颜。据此看来,拉施特所说的兀良合,就是指不儿罕山的兀良合。为了把它区别于森林兀良合,也可以称为草原兀良合。
这就是说,十世纪初以前从森林兀良合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分离出来到斡难河、土剌河流域以及不儿罕山附近游牧。兀良合部分离成为两部分。
兀良合人很早以前同蒙古孛儿只斤氏族成员建立了密切关系。特别是在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家和对外战争过程中,不儿罕山兀良合之者勒蔑、速别额台、察兀儿罕三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蒙古秘史》记载,朵奔·蔑儿干娶投靠不儿罕山兀良合的豁里剌儿台·蔑儿干之女阿阑·豁阿为妻。
成吉思·汗第九世祖孛端察儿娶札儿赤兀惕·阿当罕·兀良合妇人为妻,从此产生了孛儿只斤氏族。1162年成吉思·汗诞生时,不儿罕山兀良合之札儿赤兀歹老人特意送给珍贵的貂鼠皮襁褓。成吉思汗年轻时期,札儿赤兀歹老人将爱子者勒蔑送给他"备鞍子,开门子。"不久,速别额台、察兀儿罕也归附了成吉思·汗。
由于者勒蔑、速别额台多次立战功,当时同者别、忽必来一起被称为成吉思·汗四员猛将。在托忒蒙古文献中,不仅将脱欢太师说是者勒蔑的后裔,而且将者勒蔑父亲札儿赤兀歹老人往往与成吉思汗四兄弟相提并论。可是后来的个别回纥蒙古文献中却诬蔑者勒蔑,这可能是他的后裔也先汗夺取蒙古汗位的缘故。实际上,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家,推行千户制度,者勒蔑、速别额台、察兀儿罕等陆续被封为千户长。
同时,成吉思·汗将扈卫军扩建到一万人。者勒蔑子也孙帖额奉命统率带弓简的一千名豁儿赤。据《史集》记载,当时成吉思·汗弟哈赤温子额勒只格歹所属三千户牧地,在大兴安岭北以及后来的朵颜卫附近。他们主要由乃蛮、兀良合和塔塔儿人组成。
从后来的蒙、汉文文献记载看,这部分兀良合人首领察兀儿罕是者勒篾之长子。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后,兀良合部千户长额古迭臣及其后裔世世代代奉命守护不儿罕山大禁地,即成吉思·汗及历代元朝皇帝的葬地。额古迭臣为官职名称,汉意为把门的。也孙帖额很可能是第一任额古迭臣。据《元史·速不台传》记载,贵由汗在位的1246-1248年间,速别额台告老"还家于土剌河上"。
从这些看来,成吉思·汗逝世后不儿罕山兀良合人的多数仍在原来牧地。其中察兀儿罕为首的一部分人迁徙到大兴安岭南以后,1283年元世祖忽必烈又把一部分乞儿吉思、兀速、憨哈纳思人迁移到朵颜山附近。明代的兀良合三卫,其中特别是喀剌沁、蒙古勒津部主要是由这些人构成。这一点,奥登同志阐明得比较清楚,这里不想再重复。下面简要论证明代不儿罕山兀良合人,即也孙帖额后裔所属部落的变迁情况。
研究明代蒙古史感到最困难的是缺乏史料。由于史料缺乏,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恐怕任何人都难免。我1988年提出的有关兀良合部变迁的看法,是以蒙、满、汉、俄、波斯等多种文字史料作为依据,并参考了蒙古民俗学、语言学资料和卫拉特民间文学资料。
据多数蒙古历史文献记载,1491年达延·汗重新统一四十万蒙古后,把它划分为左右两翼各三万户。漠北左翼三万户是: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合。漠南右翼三万户是: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在《宝贝念珠》中,把漠北左翼三万户之一兀良合,作额鲁特万户。由此看来,兀良合和额鲁特是同一个部落的不同称呼。额鲁特是绰罗斯氏,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
前几年,在新疆新发现的托忒蒙古文《汗廷史》中写道:扎儿赤兀歹子者勒蔑,者勒蔑七世孙博·汗,博·汗娶霍尔穆斯塔之女生帖木儿·脱欢太师,脱欢太师成为额鲁特·汗。札儿赤兀歹、者勒蔑父子两人是十三世纪不儿罕山兀良合人,他们的后裔绰罗斯部脱欢太师当然是兀良合人。有人根本没有读过《汗廷史》,却说是后人伪造的,这是没有根据而且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大学者不能这样。
清代礼亲王昭木连 是朝廷的反对派,他著《啸亭杂录》,称准噶尔为元朝也速之后,并说了噶尔丹汗的很多好话。也速是不儿罕山兀良合人者勒蔑次子也孙帖额的简称。上面说过,兀良合和额鲁特是同一个部落的不同称呼。准噶尔就是额鲁特,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在清代蒙、汉各种文献中,往往把兀良合根据他们的所在地方或者从属关系区分为阿尔泰·兀良合、唐努·兀良合、扎萨克图·汗下兀良合,等等。在满文《呼伦贝尔总统事略》中,将额鲁特称为额鲁特·兀良合。
据汉文岷峨山人《译语》记载:兀良哈甚骁勇,负瀚海而居,虏中呼为"黄毛。"西北一部亦曰兀良哈,性质并同,但戴红帽为号。在本书原注中又写道:亦呼花当为"黄毛"。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是1517年达延·汗逝世后博迪·汗时代兀良合人的情况。
据当时地理方位,负瀚海而居的兀良合应该是指不儿罕山兀良合,西北一部兀良合可以判断在杭爱山以西阿尔泰山一带。花当是兀良合三卫人,喀喇沁部的祖先,牧地在长城东部沿边一带无疑。
在俄文《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俄国旅行家佩特林1619年经过呼和浩特到北京的途中遇见的蒙古勒津部人,均被称为黄蒙古。看来,"黄毛"是黄蒙古的误解。据托忒蒙古文《蒙古溯源史》记载,明代还有巴尔浑、不里牙惕所属兀良合。这显然是指没有从巴尔忽真·脱窟木境内迁移的原来的森林兀良合。森林兀良合是否也称为黄蒙古,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的史料记载,但在蒙古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锡拉斯-siras、锡拉惕-sirad、锡拉努惕-siranud等蒙古姓氏。它们的词根均为锡拉-sir,汉意为黄。这些蒙古姓氏除了额鲁特、喀喇沁、蒙古勒津之外,在巴尔浑、不里牙惕人中最多。这可能是森林兀良合人长期同巴尔浑、不里牙惕人杂居,并被他们同化的缘故。因此,根据以上蒙、汉、俄文各种文献可以作出下列定论:黄蒙古是渊源于兀良合的蒙古各部落的泛称。其中包括原来的森林兀良合、不儿罕山兀良合,也包括十三世纪初从不儿罕山兀良合分离出来的兀良合三卫之喀剌沁部、蒙古勒津部。
那么,蒙古博迪·汗时代在不儿罕山西阿尔泰山一带戴红帽为号的"黄毛"兀良合到底是指什么?在巴托尔·乌巴什·图们著《四卫拉特史》记载道:"自被命名为红缨卡尔梅克·卫拉特·额鲁特至今土卯年已三百八十二年"。土卯年是指本书成书的1819年。从1819年减去382年,被命名为红缨卫拉特的时间恰好是绰罗斯部脱欢太师杀四十万蒙古阿岱·汗的1437年。
内蒙古师范大学 金峰
近十多年来,我国有些权威学者曾提出兀良合是古代蒙古高原林木中百姓的"泛称"。1985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族女学者奥登同志发表《蒙古兀良哈部落的变迁》一文,对"泛称论"给予有力的驳斥,并对明代兀良合三卫诸问题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但我觉得,奥登同志对原来森林兀良合、不儿罕山兀良合的论述并不完全使人满意。
在1988年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在《兀良合部落的变迁》一文的提要中我写道:从十三世纪蒙古兴起到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汗国灭亡的五百多年期间,兀良合部发生了多次变迁,每次变迁之后兀良合一名所指的部落也有很大不同。
概括起来讲:
第一、确实从森林兀良合或草原兀良合演变过来并由原真正的兀良合人构成的部落,如绰罗斯、塔崩、鄂尔多斯、额鲁特、小额鲁特、杜尔伯特、喀喇沁、准噶尔等。
第二、因为统治者是兀良合部人而一度被称为兀良合的部落,如蒙古勒津、阿尔泰·兀良罕、唐努·兀良罕等。
第三、由于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或者荣誉的追求而被命名和冒名的兀良合部,如原秃绵·乞儿思吉之各部以及巴尔浑、不里牙惕等。
第四、由于被统治者是兀良合人而统治者自己也称为兀良合部落,如科尔沁等。
论文提要在1988年《内蒙古师大学报》第三期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不少蒙古史学者的兴趣。蒙古国科学院纳楚克·道尔吉院士认为,在提要中提出的论点确实很重要,希望早日写出全文。日本一位教授表明,提要中的某些论点他曾提出过。香港有位学者认为,近几年我发表的有些文章解决了明代蒙古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
1989年八月初,在内蒙古大学由中国蒙古史学会主持召开的明代蒙古史专题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蔡家艺同志说,在提要中提出的有关兀良合的论点确实值得研究,因为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卫拉特各鄂托克、昂吉、集赛中,特别是在鄂托克中确实有不少兀良合人。奥登同志认为,近几年我发表的论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某些论点肯定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卫拉特史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同时,部分学者对我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主要有下列三点:第一,蒙古文献不可信,特别是所谓托忒蒙古文献是由于某种政治需要而后人随意伪造的,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第二,兀良合是成吉思汗直辖部落,卫拉特是成吉思汗驸马的所属部落,二者之间根本不同,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第三,如果新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前人长期以来有关卫拉特史的研究成果全盘被否定,蒙古史需要重新写了,等等。在这里,对以上不同意见我不想一一给予答复。趁此机会,关于兀良合部落的变迁问题补充几句。
兀良合是在蒙古各部落中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部落。从十世纪初开始,在辽、金时期的汉籍中曾多次提到兀良合。据《辽史·太祖本纪》记载,十世纪初兀良合部的牧地在辽都临潢府西北,并同辽廷建立了经济关系。在拉施特《史集》中,兀良合被区分为森林兀良合和兀良合两部分,并明确提出兀良合住在巴尔忽真·脱窟木境内。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第十世祖朵奔·蔑儿干时代,豁里·秃马惕部的豁里剌儿台·蔑儿干听说不儿罕山一带便于捕猎,举家投奔了不儿罕山的主人兀良合部的晒赤·伯颜。据此看来,拉施特所说的兀良合,就是指不儿罕山的兀良合。为了把它区别于森林兀良合,也可以称为草原兀良合。
这就是说,十世纪初以前从森林兀良合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分离出来到斡难河、土剌河流域以及不儿罕山附近游牧。兀良合部分离成为两部分。
兀良合人很早以前同蒙古孛儿只斤氏族成员建立了密切关系。特别是在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家和对外战争过程中,不儿罕山兀良合之者勒蔑、速别额台、察兀儿罕三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蒙古秘史》记载,朵奔·蔑儿干娶投靠不儿罕山兀良合的豁里剌儿台·蔑儿干之女阿阑·豁阿为妻。
成吉思·汗第九世祖孛端察儿娶札儿赤兀惕·阿当罕·兀良合妇人为妻,从此产生了孛儿只斤氏族。1162年成吉思·汗诞生时,不儿罕山兀良合之札儿赤兀歹老人特意送给珍贵的貂鼠皮襁褓。成吉思汗年轻时期,札儿赤兀歹老人将爱子者勒蔑送给他"备鞍子,开门子。"不久,速别额台、察兀儿罕也归附了成吉思·汗。
由于者勒蔑、速别额台多次立战功,当时同者别、忽必来一起被称为成吉思·汗四员猛将。在托忒蒙古文献中,不仅将脱欢太师说是者勒蔑的后裔,而且将者勒蔑父亲札儿赤兀歹老人往往与成吉思汗四兄弟相提并论。可是后来的个别回纥蒙古文献中却诬蔑者勒蔑,这可能是他的后裔也先汗夺取蒙古汗位的缘故。实际上,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家,推行千户制度,者勒蔑、速别额台、察兀儿罕等陆续被封为千户长。
同时,成吉思·汗将扈卫军扩建到一万人。者勒蔑子也孙帖额奉命统率带弓简的一千名豁儿赤。据《史集》记载,当时成吉思·汗弟哈赤温子额勒只格歹所属三千户牧地,在大兴安岭北以及后来的朵颜卫附近。他们主要由乃蛮、兀良合和塔塔儿人组成。
从后来的蒙、汉文文献记载看,这部分兀良合人首领察兀儿罕是者勒篾之长子。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后,兀良合部千户长额古迭臣及其后裔世世代代奉命守护不儿罕山大禁地,即成吉思·汗及历代元朝皇帝的葬地。额古迭臣为官职名称,汉意为把门的。也孙帖额很可能是第一任额古迭臣。据《元史·速不台传》记载,贵由汗在位的1246-1248年间,速别额台告老"还家于土剌河上"。
从这些看来,成吉思·汗逝世后不儿罕山兀良合人的多数仍在原来牧地。其中察兀儿罕为首的一部分人迁徙到大兴安岭南以后,1283年元世祖忽必烈又把一部分乞儿吉思、兀速、憨哈纳思人迁移到朵颜山附近。明代的兀良合三卫,其中特别是喀剌沁、蒙古勒津部主要是由这些人构成。这一点,奥登同志阐明得比较清楚,这里不想再重复。下面简要论证明代不儿罕山兀良合人,即也孙帖额后裔所属部落的变迁情况。
研究明代蒙古史感到最困难的是缺乏史料。由于史料缺乏,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恐怕任何人都难免。我1988年提出的有关兀良合部变迁的看法,是以蒙、满、汉、俄、波斯等多种文字史料作为依据,并参考了蒙古民俗学、语言学资料和卫拉特民间文学资料。
据多数蒙古历史文献记载,1491年达延·汗重新统一四十万蒙古后,把它划分为左右两翼各三万户。漠北左翼三万户是: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合。漠南右翼三万户是: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在《宝贝念珠》中,把漠北左翼三万户之一兀良合,作额鲁特万户。由此看来,兀良合和额鲁特是同一个部落的不同称呼。额鲁特是绰罗斯氏,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
前几年,在新疆新发现的托忒蒙古文《汗廷史》中写道:扎儿赤兀歹子者勒蔑,者勒蔑七世孙博·汗,博·汗娶霍尔穆斯塔之女生帖木儿·脱欢太师,脱欢太师成为额鲁特·汗。札儿赤兀歹、者勒蔑父子两人是十三世纪不儿罕山兀良合人,他们的后裔绰罗斯部脱欢太师当然是兀良合人。有人根本没有读过《汗廷史》,却说是后人伪造的,这是没有根据而且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大学者不能这样。
清代礼亲王昭木连 是朝廷的反对派,他著《啸亭杂录》,称准噶尔为元朝也速之后,并说了噶尔丹汗的很多好话。也速是不儿罕山兀良合人者勒蔑次子也孙帖额的简称。上面说过,兀良合和额鲁特是同一个部落的不同称呼。准噶尔就是额鲁特,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在清代蒙、汉各种文献中,往往把兀良合根据他们的所在地方或者从属关系区分为阿尔泰·兀良合、唐努·兀良合、扎萨克图·汗下兀良合,等等。在满文《呼伦贝尔总统事略》中,将额鲁特称为额鲁特·兀良合。
据汉文岷峨山人《译语》记载:兀良哈甚骁勇,负瀚海而居,虏中呼为"黄毛。"西北一部亦曰兀良哈,性质并同,但戴红帽为号。在本书原注中又写道:亦呼花当为"黄毛"。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是1517年达延·汗逝世后博迪·汗时代兀良合人的情况。
据当时地理方位,负瀚海而居的兀良合应该是指不儿罕山兀良合,西北一部兀良合可以判断在杭爱山以西阿尔泰山一带。花当是兀良合三卫人,喀喇沁部的祖先,牧地在长城东部沿边一带无疑。
在俄文《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俄国旅行家佩特林1619年经过呼和浩特到北京的途中遇见的蒙古勒津部人,均被称为黄蒙古。看来,"黄毛"是黄蒙古的误解。据托忒蒙古文《蒙古溯源史》记载,明代还有巴尔浑、不里牙惕所属兀良合。这显然是指没有从巴尔忽真·脱窟木境内迁移的原来的森林兀良合。森林兀良合是否也称为黄蒙古,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的史料记载,但在蒙古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锡拉斯-siras、锡拉惕-sirad、锡拉努惕-siranud等蒙古姓氏。它们的词根均为锡拉-sir,汉意为黄。这些蒙古姓氏除了额鲁特、喀喇沁、蒙古勒津之外,在巴尔浑、不里牙惕人中最多。这可能是森林兀良合人长期同巴尔浑、不里牙惕人杂居,并被他们同化的缘故。因此,根据以上蒙、汉、俄文各种文献可以作出下列定论:黄蒙古是渊源于兀良合的蒙古各部落的泛称。其中包括原来的森林兀良合、不儿罕山兀良合,也包括十三世纪初从不儿罕山兀良合分离出来的兀良合三卫之喀剌沁部、蒙古勒津部。
那么,蒙古博迪·汗时代在不儿罕山西阿尔泰山一带戴红帽为号的"黄毛"兀良合到底是指什么?在巴托尔·乌巴什·图们著《四卫拉特史》记载道:"自被命名为红缨卡尔梅克·卫拉特·额鲁特至今土卯年已三百八十二年"。土卯年是指本书成书的1819年。从1819年减去382年,被命名为红缨卫拉特的时间恰好是绰罗斯部脱欢太师杀四十万蒙古阿岱·汗的1437年。
内蒙古师范大学 金峰
2017年1月9日星期一
内蒙新巴尔虎网络联署号召人被带走 大批牧民派出所要人被喷辣椒水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500多名牧民,日前在网络上发起联署,抗议旗政府克扣牧业补贴款,不料信件发出后,四名联署号召人被旗公安局带走失联。为此,大批牧民日前自发围堵到派出所要求放人,却遭警方喷洒辣椒水驱散。
据了解,被警方带走的四名联署号召人中还有一名正在哺乳期的孩子妈妈,而她的孩子只有4个月大。
一名当地的维权人士接受本台采访时称,牧民因遭灾向政府反映问题,要求一次性发放克扣的禁牧补贴款,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但旗政府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对反映问题的牧民严加防范:
“昨天开始就已经找当地的牧民,警察叫他们,就是要查网上谁发的帖子,这些人因为发帖被叫去以后还有些哺乳期的妇女,最后很多牧民去了还遭辣椒水喷了,说有毒、很难受,当时有人晕了,被急救车带走了,警方怕闹大了,把这几个人放了,至于那四个人放没放我不清楚,警察恐吓他们,一般呼盟地区都这么干,去年维权也是这样的,最后把当地的老百姓看住,不让消息外泄。”
本台早前曾报道,新巴尔虎右旗的500多名牧民日前发布联署信指,今年冬季的雪灾给牧民造成极大损失且冬季储草价格昂贵,政府发放的救济饲料因质量太差牛羊根本不吃。为了维持生计,几乎家家借债,因国家贷款不够用,许多牧民还借了高利贷,但政府却克扣牧民的救命钱。眼看2016 年已经过去了,但新巴尔虎右旗的牧业补贴款还不见发放,牧民们多次到当局了解情况,旗财政局指拨款已到位,但牧民们却只收到4成禁牧补贴款和草畜平衡补贴款,余下的补贴款当局一直不发放,且拒绝作出任何解释。
记者在网上查看发现,当地牧民用母语写的请愿书,落款是新右旗全体牧民,共同上载的还有牧民们的签名及正在签名的照片。但目前这封该联署信及相关帖子已经遭到全网删除。
记者向关押牧民的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查询,但对方在得知记者身份后拒绝透露任何情况。
记者又向新巴尔虎右旗政府查询,一名值班人员要记者找发改局了解情况:“克扣补贴这个事你给发改局打个电话吧。”
记者:“据说上访好多次了,之前说给,后来食言了,
值班人员: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事,他们具体跟着上访就找谁去吧。”
而信访局的接线人员则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当地一名维权人士告诉本台,当局正在采取分化方式打击牧民维权:
“有专门公安下来说,说不准接受外媒采访,他们就咽不下这口气,现在内蒙很多地方财政赤字,没有钱,说没办法,我们现在公务员都没发,工资挪用一下怎么样,他们也有办法,老百姓不知道的情况下钱就被挪用了,这就是现状。中国现在自上而下整个就是腐败,老百姓在强权面前无能为力,结果就不说话了,有人被分化了,给钱的给钱,关押的关押。”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石山/嘉远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
内蒙翁牛特旗牧民再上访 新巴尔虎牧民联署抗议 - RFA
内蒙古翁牛特旗日前再有十多人为玉米补贴被克扣而继续维权,但又被当局敷衍。此外,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部分牧民,因不满当地政府克扣牧业补贴款,而在网上发出联署控告信。此外,早前到林业厅抗议旗政府克扣专项补贴款的的翁牛特旗护林员,遭到森林公安报复,有消息称他们正面临解聘。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十多名牧民1月4日再次到赤峰市政府请愿,要求发放被克扣的玉米差价补贴。去年11月,翁牛特旗两个镇的150多位牧民曾举行大集访,官员终于答应补发补贴,但牧民散去后,当地政府却拒绝兑现承诺。
关注事件的当地维权人士告诉本台,对于当局食言,牧民感到愤怒,准备到北京告状:
“关于玉米补贴的问题,现在他们去赤峰了,从旗里头的信访局从翁牛特到赤峰很远的路。维权代表刘海秋是种粮大户,他种了660亩,给他发了189亩补贴,后来他领着大家维权,政府说再跟给你200亩的补贴。现在就这么干,就是拖欠。整个赤峰市14个亿他们是种植基地,钱多,种 的少的地方克扣容易被发现,钱多的地方他们就容易挪用。这次来十个人,不行再去北京。”
记者就此致电翁牛特旗信访局,接线人员表示自己去年还没有在信访局工作,对当局向牧民的承诺不知情:
翁牛特旗信访局:“玉米款我不清楚,没来我们这说过。”
记者:“据说上访好几次了。”
翁牛特旗信访局:“我不清楚,我们从来没接过玉米什么补贴款的项目,今年都没有要玉米款补贴来过我们这。”
记者:“是去年承诺的。”
翁牛特旗信访局:“去年我还没来信访局工作呢。”
同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牧民发起网络联署,抗议当局克扣牧业补贴款,联署信指,今年冬季的雪灾给牧民造成极大损失且冬季储草价格昂贵,政府发放的救济饲料因质量太差牛羊根本不吃。为了维持生计几乎家家有贷款,因国家贷款不够用,许多牧民还借了高利贷,但政府却克扣牧民的救命钱。
联署信称,眼看2016 年已经过去了,但新巴尔虎左旗的牧业补贴款还不见发放,牧民们多次到当局了解情况,旗财政局指拨款已到位,但牧民们却只收到4成禁牧补贴款和草畜平衡补贴款,余下的补贴款当局一直不发放且拒绝作出任何解释。
记者就此致电新巴尔虎左旗政府,一名值班人员表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文件室,来回弄文件, 然后弄会,。我不太清楚,这个是你问一下信访局。”
而信访局的接线人员则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在网上看到当地牧民用母语写的请愿书,落款是新右旗全体牧民,共同上载的还有牧民们的签名及正在签名的照片。
此外,1月4日翁牛特旗的两位护林员代表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向林业厅抗议旗政府数年来擅自挪用森林补偿款7千多万元后,翁牛特旗的森林公安派出所所长丁向东找到部分签名的护林员,宣布全部解聘。
一名当地的维权人士告诉本台,这就是当局赤裸裸的报复行动,呼吁外界关注:
“(维权代表)照日格图他们俩说当地的老百姓来电话,现在他们那的森林公安已经表态,这19个护林员全部不让干了,这就是报复。”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吴晶
2017年1月5日星期四
蒙古首都PM2.5一度逼近2000 政府宣布夜间用电免费
在中国北方备受雾霾困扰之际,中国的邻国——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空气问题更为严重,到了持续爆表的程度。为了鼓励当地居民使用电热器,而不是通过烧煤、木炭或其他燃料取暖,蒙古国政府决定自今年1月1日起不再征收夜间电费。
彭博社此前曾报道,为鼓励居民多使用电热器,蒙古国政府早前把该国的夜间电价削减了50%。由于效果并不明显,蒙古国总理扎尔格勒图勒嘎•额尔登巴特(Erdenebat Jargaltulga)于2016年12月23日表示,自2017年1月1日起不再征收夜间电费。
乌兰巴托气候寒冷,冬季时间超过6个月,取暖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半数以上的乌兰巴托市民居住在城市北部的棚户区,那里基本上没有集中供暖,很多居民靠在家中烧煤、木炭等取暖。这种取暖的方式将会导致雾霾更加严重,乌兰巴托冬季每天早晚城市空气中都会弥漫着呛人的味道。乌兰巴托也被多家国际媒体称为全世界冬季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数据显示,乌兰巴托的PM2.5值高得惊人。澎湃新闻在蒙古国的政府网站agaar.mn上发现,1月4日乌兰巴托Bayankhoshuu的PM2.5最高值为1470μg/m3,当天的PM2.5平均水平为697μg/m3。在2016年12月16日,乌兰巴托Bayankhoshuu棚户区PM2.5水平曾一度飙升至1985μg/m3,当天PM2.5的24小时平均水平则达到了1071μg/m3。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给出的PM2.5的24小时平均水平的安全值是25μg/m3,乌兰巴托则为其40倍。
额尔登巴特在一份政府声明中称,政府治污的长远举措包括把容纳了数十万人口、用蒙古包搭建的临时棚户区改建为公寓住宅区,以及大力鼓励居民用电取暖,并通过地方扶贫来减少流入首都的人口。彭博社报道称,经济增长紧缩和预算赤字上的增加让蒙古国政府几乎没有财力来对抗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蒙古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中国等伙伴寻求经济救援。
蒙古国政府应对污染问题的方式单一,政策力度不到位,令公众很是不满。彭博社报道称,蒙古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 of Mongolia)的负责人巴央加噶尔•比央巴塞可汗(Byambasaikhan Bayanjargal)表示,他和家人平时都尽量待在室内,周末就出城去。“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变,实在令人丧气”,他说,“我们需要一贯的政策和稳定,这样业界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同事的小孩中大多数不是在住院,就是在家忍受呼吸道疾病的折磨”,蒙古国电视台(Mongol TV station)的新闻主任额尔德尼•拉格瓦(Lhagva Erdene)在电子邮件中护肤彭博社时表示,“我们对政府的无所作为感到无奈和沮丧。”
2016年12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发出警告称,如果不控制空气污染水平,一场危机迫在眉睫,五岁以下的儿童和未出生的胎儿是面临风险最严峻的群体。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乌兰巴托10%的死亡案例和空气污染引起的并发症有关。
据新华社日前报道,由于不堪雾霾的困扰以及对政府治霾政策的不满,2016年12月26日,数百名蒙古国民众在首都乌兰巴托举行反雾霾抗议行动,呼吁政府和社会重视乌兰巴托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采取切实措施提升空气质量。(澎湃新闻)
彭博社此前曾报道,为鼓励居民多使用电热器,蒙古国政府早前把该国的夜间电价削减了50%。由于效果并不明显,蒙古国总理扎尔格勒图勒嘎•额尔登巴特(Erdenebat Jargaltulga)于2016年12月23日表示,自2017年1月1日起不再征收夜间电费。
乌兰巴托气候寒冷,冬季时间超过6个月,取暖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半数以上的乌兰巴托市民居住在城市北部的棚户区,那里基本上没有集中供暖,很多居民靠在家中烧煤、木炭等取暖。这种取暖的方式将会导致雾霾更加严重,乌兰巴托冬季每天早晚城市空气中都会弥漫着呛人的味道。乌兰巴托也被多家国际媒体称为全世界冬季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数据显示,乌兰巴托的PM2.5值高得惊人。澎湃新闻在蒙古国的政府网站agaar.mn上发现,1月4日乌兰巴托Bayankhoshuu的PM2.5最高值为1470μg/m3,当天的PM2.5平均水平为697μg/m3。在2016年12月16日,乌兰巴托Bayankhoshuu棚户区PM2.5水平曾一度飙升至1985μg/m3,当天PM2.5的24小时平均水平则达到了1071μg/m3。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给出的PM2.5的24小时平均水平的安全值是25μg/m3,乌兰巴托则为其40倍。
额尔登巴特在一份政府声明中称,政府治污的长远举措包括把容纳了数十万人口、用蒙古包搭建的临时棚户区改建为公寓住宅区,以及大力鼓励居民用电取暖,并通过地方扶贫来减少流入首都的人口。彭博社报道称,经济增长紧缩和预算赤字上的增加让蒙古国政府几乎没有财力来对抗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蒙古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中国等伙伴寻求经济救援。
蒙古国政府应对污染问题的方式单一,政策力度不到位,令公众很是不满。彭博社报道称,蒙古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 of Mongolia)的负责人巴央加噶尔•比央巴塞可汗(Byambasaikhan Bayanjargal)表示,他和家人平时都尽量待在室内,周末就出城去。“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变,实在令人丧气”,他说,“我们需要一贯的政策和稳定,这样业界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同事的小孩中大多数不是在住院,就是在家忍受呼吸道疾病的折磨”,蒙古国电视台(Mongol TV station)的新闻主任额尔德尼•拉格瓦(Lhagva Erdene)在电子邮件中护肤彭博社时表示,“我们对政府的无所作为感到无奈和沮丧。”
2016年12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发出警告称,如果不控制空气污染水平,一场危机迫在眉睫,五岁以下的儿童和未出生的胎儿是面临风险最严峻的群体。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乌兰巴托10%的死亡案例和空气污染引起的并发症有关。
据新华社日前报道,由于不堪雾霾的困扰以及对政府治霾政策的不满,2016年12月26日,数百名蒙古国民众在首都乌兰巴托举行反雾霾抗议行动,呼吁政府和社会重视乌兰巴托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采取切实措施提升空气质量。(澎湃新闻)
内蒙翁牛特旗600护林员代表赴林业厅上访 抗议截留补偿款 - RFA
内蒙古翁牛特旗的两位代表,带着600多名公益护林员的联署公开信前往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向林业厅上访,抗议旗政府数年来擅自挪用森林补偿款7千多万元。两位代表表示,此前护林员们多次到各级政府上访均遭到推诿,政府部门官官相护,拒绝受理,他们无奈之下才长途跋涉到自治区告状。
翁牛特旗格日僧苏木的维权护林员代表照日格图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国家2013和2014年两年增补的每亩2.5元的补贴款,他们至今也没得到。
照日格图:“我们今天上去林业厅。”
记者:“现在有没有官员见你们?”
照日格图:“没有官员接见我们。他们挪用了专项拨款。”
记者:“挪用了多少钱?”
照日格图:“7000多万。”
记者:“挪用了你们几年的补贴款?”
照日格图:“13年到14年的补贴款都没有给我们。”
照日格图还告诉本台,关于2016年被扣的补贴款,旗林业局回复指这部分钱已经给所有护林员统一交了养老保险,但有人到社保局核实后直接戳穿的了当局的谎言。
照日格图:“16年也扣了我们的钱,当时说是给交了养老保险,但是我们去社保局查,发现他们没给我们上保险。”
记者:“你们代表多少护林员?”
照日格图:“现在是我们两个上访,但是代表了600多个护林员。”
记者就此致电翁牛特旗政府,但接线人员拒绝接受采访,而自治区林业局的电话则无人接听。
帮助维权代表写上访材料的一名当地维权人士接受本台采访时称,翁牛特旗政府无法无天,生活在这里的牧民、农民都苦不堪言,多次因不同事件上访,此次信访局指他们是违法“接力上访”:
“现在中国真的不行了,共产党的官不干正经的,就贪老百姓的那一点钱,老百姓也看出来了不抗争没法活。他们昨天晚上来的,今天我们去林业厅告状和信访局,吓得他们说你们现在是搞接力是不是?翁牛特地区前一阵是养猪问题,后来是辽河油田的问题,前一阵是玉米补贴问题,现在又是护林员问题。护林员有几百人,他们是代表,当地牧民很有维权意识。”
当地维权人士还表示,当天除了翁牛特旗护林员之外,还有乌拉特旗被克扣玉米补贴的牧民在场抗议,但因为害怕遭到当局报复,这些人已经被迫返回:
“实际上这次翁牛特来了,同时乌拉特也来了,但是乌拉特的代表们害怕,结果就没说。他们现在回去了征集签名,可能涉及到好几万人。这些嘎查属于种试基地,他之所以克扣就是因为钱多。内蒙地区拨了86亿,赤峰地区14个亿,至于翁牛特多少我不太清楚,他们去问政府也不说,说到底就是挪用。”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吴晶
翁牛特旗格日僧苏木的维权护林员代表照日格图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国家2013和2014年两年增补的每亩2.5元的补贴款,他们至今也没得到。
照日格图:“我们今天上去林业厅。”
记者:“现在有没有官员见你们?”
照日格图:“没有官员接见我们。他们挪用了专项拨款。”
记者:“挪用了多少钱?”
照日格图:“7000多万。”
记者:“挪用了你们几年的补贴款?”
照日格图:“13年到14年的补贴款都没有给我们。”
照日格图还告诉本台,关于2016年被扣的补贴款,旗林业局回复指这部分钱已经给所有护林员统一交了养老保险,但有人到社保局核实后直接戳穿的了当局的谎言。
照日格图:“16年也扣了我们的钱,当时说是给交了养老保险,但是我们去社保局查,发现他们没给我们上保险。”
记者:“你们代表多少护林员?”
照日格图:“现在是我们两个上访,但是代表了600多个护林员。”
记者就此致电翁牛特旗政府,但接线人员拒绝接受采访,而自治区林业局的电话则无人接听。
帮助维权代表写上访材料的一名当地维权人士接受本台采访时称,翁牛特旗政府无法无天,生活在这里的牧民、农民都苦不堪言,多次因不同事件上访,此次信访局指他们是违法“接力上访”:
“现在中国真的不行了,共产党的官不干正经的,就贪老百姓的那一点钱,老百姓也看出来了不抗争没法活。他们昨天晚上来的,今天我们去林业厅告状和信访局,吓得他们说你们现在是搞接力是不是?翁牛特地区前一阵是养猪问题,后来是辽河油田的问题,前一阵是玉米补贴问题,现在又是护林员问题。护林员有几百人,他们是代表,当地牧民很有维权意识。”
当地维权人士还表示,当天除了翁牛特旗护林员之外,还有乌拉特旗被克扣玉米补贴的牧民在场抗议,但因为害怕遭到当局报复,这些人已经被迫返回:
“实际上这次翁牛特来了,同时乌拉特也来了,但是乌拉特的代表们害怕,结果就没说。他们现在回去了征集签名,可能涉及到好几万人。这些嘎查属于种试基地,他之所以克扣就是因为钱多。内蒙地区拨了86亿,赤峰地区14个亿,至于翁牛特多少我不太清楚,他们去问政府也不说,说到底就是挪用。”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吴晶
达瓦才仁解读蒙古不欢迎达赖喇嘛 - RFA
纽约时报引述报导指蒙古国外交部长对允许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到访感到抱歉,并宣称现任政府将不欢迎达赖喇嘛再次访问蒙古。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表示,了解也尊重蒙古国所作决定,这对西藏和达赖喇嘛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北京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去年11月访问蒙古国持续施压,纽约时报中文网3号以“蒙古不再欢迎达赖喇嘛,切割数百年文化纽带”为题,引述报导蒙古国外交部长表明拒绝达赖喇嘛再次访问蒙古的态度。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达瓦才仁指出,这是全球性对中国大陆政府妥协的一部份,很多欧洲国家,甚至连像蒙古国让达赖喇嘛访问都不敢尝试。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说:“他邀请达赖喇嘛,然后在邀请达赖喇嘛的过程中,他就在他的宗教文化的复兴这些方面达到了目的,然后再回过头来跟中国说好话,以达到他的经济目的,所以从蒙古的角度,他其实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达瓦才仁表示,蒙古和西藏有密切地宗教文化的精神连系,蒙古又是夹在俄罗斯和大陆的内陆国,与他们有非常强的经济连系,是中国大陆政府一定要蒙古在两难之间作选择,蒙古只能用这种方式去维护利益。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说:“全世界除了美国、日本以外,其他所有的国家好像都是,你像以前比如说南非,达赖喇嘛参加诺贝尔和平奖,南非都不敢给达赖喇嘛签证,那南非跟中国很遥远,而蒙古就在旁边,蒙古而且更弱小,所以说,一直都是这样。”
达瓦才仁说,达赖喇嘛一般不会回应,也不认为这对西藏是个问题。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札西慈仁受访表示:“好几年的历史上面,就是有蒙古跟西藏有关系的,还有特别在藏传佛教上面来讲,今天全世界认的达赖喇嘛,这个达赖喇嘛这是蒙古人取的名字嘛,所以我们的关系是没办法那么容易被中共破坏。”
札西认为,蒙古此时表态,是因为达赖喇嘛正在印度进行金刚灌顶法会,他才从印度返回台湾,眼见中国大陆政府强力介入,把汉、藏佛教徒赶走。
法新社4号报导,七千人迫于大陆政府的威胁,在法会开始前返回西藏。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说:“对一般的西藏人,他可能只是握有护照,他根本没有想去参加这些法会的,你竟然把护照收回去,由警察替你保管,这些都是一种伤害的动作。”
达瓦才仁认为,北京以伤害的动作,争取藏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或是接受大陆对西藏的殖民统治,都没有任何好处,这是愚蠢的作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台北报道
蒙古不再欢迎达赖喇嘛,切割数百年文化纽带 - 纽约时报
蒙古国的统治者曾在达赖喇嘛制度于数百年前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这片土地已经不再欢迎他。
蒙古国外交部长于上月发表的言论,是又一个国家迫于来自中国的压力在关于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争议性问题上低头的最新迹象。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称,曾德·蒙赫-奥尔吉勒(Tsend Munkh-Orgil)部长告诉《今日报》(Onoodor):曾于去年11月允许达赖喇嘛到访的政府对此“感到抱歉”;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达赖喇嘛“恐怕不会再次到访蒙古国了”。据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报道,蒙古国外交部证实了这番言论。
蒙古国的反应让某些学者感到惊讶,因为该国和达赖喇嘛有着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的深厚渊源。就连这个称号也暗示着两者之间的渊源:达赖在蒙古语里是“海洋”的意思。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表示了抗议,虽然这次始于11月18日、历时四天的访问,并非是在蒙古国政府邀请下成行,而且是宗教性质的。作为回应,中国取消了与蒙古国高级官员的会谈。
中国一直在向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施压,要求它们禁止在印度过着流亡生活的达赖喇嘛到访。中共领导人将达赖喇嘛视为倡导藏独的敌人,尽管他说自己只想为藏人争取更大自治权。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国对这个邻国的回应是可以预测的。蒙古国正忙于应对金融问题,并寻求从北京获得大笔贷款。得益于采矿业的发展,蒙古国经济原本一直处于突飞猛进的状态,直到不久前崩盘。
但与此同时,蒙古国一直竭力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距离,还成为了美国的军事盟友。
它也是一个传统佛教国家,与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历史有着悠久的联系,外交部长的话使一些历史学家和西藏倡导者感到震惊。
“在处理来自中国的某些压力方面,几乎全球的外交能力都在出现失控,这件事也是其中一部分。当然,一个小型内陆邻国对于中国的压力要比那些大国更加敏感,”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史学家罗伯特·J·巴尼特(Robert J. Barnett)在电子邮件中说。
首尔延世大学的中国历史学家鲁乐汉(John Delury)发推文表示,蒙古的反应“具有讽刺性,因为发明达赖喇嘛制度的正是一位蒙古大汗。”
达赖喇嘛制度起源于16世纪的蒙古领袖俺答汗,当时中国由明朝的汉族皇帝统治,俺答汗控制着与中国北部相邻的区域。
在此三个世纪之前,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代)开国皇帝忽必烈汗已经开始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并且请了一位藏人老师。
但是,俺答汗使藏传佛教成了蒙古的官方宗教。那是在1577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黄教)的领袖访问了他。那一次,俺答汗把这位精神领袖册封为达赖喇嘛。达赖在蒙古语里是“海洋”的意思,“喇嘛”是西藏的精神导师,这个称号意为“智慧的海洋”。
这一举动让蒙古人和藏人联合起来,并建立了蒙古统治者和格鲁派之间的关系。从那时起,达赖喇嘛的位子就与亚洲复杂的政治局势联系在一起了。访问俺答汗的那位格鲁派领袖之前的两任格鲁派领袖也被追封为达赖喇嘛。
因此,从俺答汗那里获得达赖喇嘛称号的那位格鲁派领袖是第三世达赖喇嘛,他法名索南嘉措(Sonam Gyatso),1588年在蒙古地区去世。之后,俺答汗的重孙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被西藏的高级喇嘛指定为第四世达赖及索南嘉措的转世(每位达赖喇嘛都被视为上一位达赖的转世),云丹嘉措是唯一被选为达赖喇嘛转世的蒙古人。
达赖喇嘛对蒙古的访问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许多人开始猜测目前这位第14世达赖喇嘛去世后,他的转世将出现在何时何地。今年81岁的达赖喇嘛说,他可能是最后一世达赖喇嘛,同时他的转世依然有着各种可能性――他也可能在西藏地区以外的地方转世,共产党领导人毫无疑问会试图在西藏地区控制任何尚未就任的转世者。
有人说,下一世达赖喇嘛会转世在印度东北部的达旺地区,那里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的故乡。达旺也恰好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个有争议的地带,中国声称那里是它的领土。
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达赖喇嘛最近的这次访问表明,蒙古可能也有希望,特别是考虑到第三世和第四世达赖喇嘛的历史。
“达赖喇嘛访问的有趣之处是,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他的转世可能出现在那里,”巴尼特说。他补充说,鉴于中国的敌意,这“对于蒙古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
蒙古国外交部长于上月发表的言论,是又一个国家迫于来自中国的压力在关于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争议性问题上低头的最新迹象。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称,曾德·蒙赫-奥尔吉勒(Tsend Munkh-Orgil)部长告诉《今日报》(Onoodor):曾于去年11月允许达赖喇嘛到访的政府对此“感到抱歉”;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达赖喇嘛“恐怕不会再次到访蒙古国了”。据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报道,蒙古国外交部证实了这番言论。
蒙古国的反应让某些学者感到惊讶,因为该国和达赖喇嘛有着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的深厚渊源。就连这个称号也暗示着两者之间的渊源:达赖在蒙古语里是“海洋”的意思。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表示了抗议,虽然这次始于11月18日、历时四天的访问,并非是在蒙古国政府邀请下成行,而且是宗教性质的。作为回应,中国取消了与蒙古国高级官员的会谈。
中国一直在向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施压,要求它们禁止在印度过着流亡生活的达赖喇嘛到访。中共领导人将达赖喇嘛视为倡导藏独的敌人,尽管他说自己只想为藏人争取更大自治权。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国对这个邻国的回应是可以预测的。蒙古国正忙于应对金融问题,并寻求从北京获得大笔贷款。得益于采矿业的发展,蒙古国经济原本一直处于突飞猛进的状态,直到不久前崩盘。
但与此同时,蒙古国一直竭力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距离,还成为了美国的军事盟友。
它也是一个传统佛教国家,与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历史有着悠久的联系,外交部长的话使一些历史学家和西藏倡导者感到震惊。
“在处理来自中国的某些压力方面,几乎全球的外交能力都在出现失控,这件事也是其中一部分。当然,一个小型内陆邻国对于中国的压力要比那些大国更加敏感,”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史学家罗伯特·J·巴尼特(Robert J. Barnett)在电子邮件中说。
首尔延世大学的中国历史学家鲁乐汉(John Delury)发推文表示,蒙古的反应“具有讽刺性,因为发明达赖喇嘛制度的正是一位蒙古大汗。”
达赖喇嘛制度起源于16世纪的蒙古领袖俺答汗,当时中国由明朝的汉族皇帝统治,俺答汗控制着与中国北部相邻的区域。
在此三个世纪之前,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代)开国皇帝忽必烈汗已经开始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并且请了一位藏人老师。
但是,俺答汗使藏传佛教成了蒙古的官方宗教。那是在1577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黄教)的领袖访问了他。那一次,俺答汗把这位精神领袖册封为达赖喇嘛。达赖在蒙古语里是“海洋”的意思,“喇嘛”是西藏的精神导师,这个称号意为“智慧的海洋”。
这一举动让蒙古人和藏人联合起来,并建立了蒙古统治者和格鲁派之间的关系。从那时起,达赖喇嘛的位子就与亚洲复杂的政治局势联系在一起了。访问俺答汗的那位格鲁派领袖之前的两任格鲁派领袖也被追封为达赖喇嘛。
因此,从俺答汗那里获得达赖喇嘛称号的那位格鲁派领袖是第三世达赖喇嘛,他法名索南嘉措(Sonam Gyatso),1588年在蒙古地区去世。之后,俺答汗的重孙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被西藏的高级喇嘛指定为第四世达赖及索南嘉措的转世(每位达赖喇嘛都被视为上一位达赖的转世),云丹嘉措是唯一被选为达赖喇嘛转世的蒙古人。
达赖喇嘛对蒙古的访问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许多人开始猜测目前这位第14世达赖喇嘛去世后,他的转世将出现在何时何地。今年81岁的达赖喇嘛说,他可能是最后一世达赖喇嘛,同时他的转世依然有着各种可能性――他也可能在西藏地区以外的地方转世,共产党领导人毫无疑问会试图在西藏地区控制任何尚未就任的转世者。
有人说,下一世达赖喇嘛会转世在印度东北部的达旺地区,那里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的故乡。达旺也恰好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个有争议的地带,中国声称那里是它的领土。
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达赖喇嘛最近的这次访问表明,蒙古可能也有希望,特别是考虑到第三世和第四世达赖喇嘛的历史。
“达赖喇嘛访问的有趣之处是,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他的转世可能出现在那里,”巴尼特说。他补充说,鉴于中国的敌意,这“对于蒙古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
2017年1月2日星期一
《李守信自述》之“我镇压嘎达梅林起义部队的经过
李守信(1892-1970) - 内蒙古文史资料《李守信自述》之“我镇压嘎达梅林起义部队的经过”
嘎达梅林,蒙名老嘎达,是哲里木盟达尔罕王旗(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带兵梅林,汉名孟青山,所以又称为孟梅林。他因反对出放蒙地,惹本旗王爷恼怒,将他关在土牢里,准备捏造罪状,把他处死。嘎达有两个老婆,二的名叫牡丹,会使手枪。她联络的四五名亲属,打开徒劳将丈夫救出。从此嘎达被王爷逼上梁山,便组织了许多牧民,展开武装斗争,震动了整个科尔沁部和辽宁热和边境。由于牧民缺乏革命经验和战斗装备,必须联合马贼(旧中国时东北的蒙族土匪)来对付王府的“小队”(旧中国时东部蒙旗衙门或札萨克的武装),难免有不少坏分子被吸收进去,将牧民奇异的性质变成流寇式的活动。嘎达无法制止,最后被我智慧的东北骑兵第十七旅全部消灭。
此事发生于何年何月,我已记不清准确时间。战争的结束,则记得是一九三零年农历二月二十四。那时张学良已经继承他的父亲张作霖通知了东北四省。他和热和政府主席汤玉麟部站在王爷一边。所以嘎达起义后,辽宁拍张海鹏部骑兵有洮南向西追击,热河电告开鲁的第十七旅崔兴武部到鲁北从东防堵,以期把嘎达的部队包围解决。我那时任崔兴武部三十四团团长。这一年冰雪很大,崔旅长养尊处优,不肯亲自出动;四十一团团长孙寿卿在开鲁装病,根本没有随军前往;二十七团团长孙凤阁,到了鲁北也躲在烧锅房(酒坊)图舒服去了。因为我好大喜功,这三个团骑兵共一千多人,全归我带领指挥。我那一团人是由马贼和胡匪组成的。嘎达梅林遇见我这个对头,不仅全军在热河的扎鲁特旗遭到覆没,连他本人也被我亲手击毙在北老哈河里。
嘎达梅林的队伍共有七百多人。他们因为被张海鹏压迫的不能在科尔沁部存留,企图沿着草地畔子,在热河北部大小巴林旗的坝前整休。坝后下了四五尺深的大学,察哈尔省乌珠穆沁旗的牧民赶着牲畜和车辆在坝前之气帐幕放牧。乌珠穆沁的牧民相当富有,携带着大量的白面、炒米。嘎达梅林计划利用这一部分给养,在哪里度过严寒的动机。张海鹏部,粮饷非常充足,官兵都不愿意吃苦受罪,将嘎达梅林的部队赶到达尔罕旗的草地即停止前进。崔兴武部是有热河游击马队编成,是东北军中的游杂队伍。官兵都想利用打仗发财,所以越省进入达尔罕旗北部。我从鲁北出发时,判断嘎达梅林必然要采用民国初年的“蒙匪”战术。在他们被张海鹏部赶到草地畔子被我堵住以后,即紧紧“焊上”跟着不放松一布,形成他们做熟饭,我们赶上去端碗,使他们没有喘息的余地。否则,他们空室清野,我们找不到食物,便会越追越远。
达尔罕旗和热河东北部的几个蒙旗,地形越往北越宽广,越往南越狭窄。由于北面的牧区人烟稀少,牧民听见嘎达梅林的部队过来,恐怕抓人赶马,都以“联庄”(各村联合)的形式开出民团戒备。因此嘎达梅林的队伍只好在中间的半农半牧区,南北有四五十里的空间地带自东向西流动。在一个名叫土列毛都的村子附近,我们把嘎达梅林的队伍截住,经学堂地(村名)和东西巨勒克(村名)往西直追。一白天追越了五个旗的境界。追到林东北面以后,我感觉这样追不是办法,因为他们能赶牧民的马群,骑累了可以更换,所以跑得更快,这样他们必然会走脱。同时我知道乌珠穆沁有七八百“小队”,在大小巴林旗的坝底下保护牲畜,决不让嘎达梅林的部队过去就食,一定要进行抵抗。我不分昼夜追赶三天,官兵都把手指冻坏,腹部全部冻成铁青,很难在追到大坝底下,同乌珠穆沁的“小队”夹击他们。于是决定转进土列毛都,以逸待劳,等他们从坝底碰壁回来再在这个地方将他们一网打尽。
嘎达梅林被我追了几天,以为我一直在他们后边跟着。当他们在龙头山北乌珠穆沁的“小队”顶住,不得不由西向东折返。因为来时的路上已经抢掠一空,又怕碰见我的队伍,于是朝北沿着牧区的边缘退却。嘎达梅林的队伍走到土列毛都附近,郁郁周围再没有村庄,两条路在这里归到一起,必须进村休息。我撤至土列毛都,对外进行了严密封锁,所以嘎达梅林不知道我们驻在这里,冒然走进我的埋伏圈内。当时正是半晌前的时候,我暸见一片黄尘底下来了一千多穿着汉族妇女红绿衣裳的“乌合之众”,以扇面队形向土列毛都跑来。走到临近,我朝天打了一排手枪子弹,士兵全上马追击,一口气冲了七十多里,在东巨勒克川把他们打散。除沿途被击毙的俘虏二三百人外,一些徒手的被东巨勒克川的农牧民用铁锹劈死。马匹东西被我们掳获,士兵们捡“洋捞”捡得忘了寒冷。
中午,嘎达梅林利用我们打尖的时候,把剩下的二三百人都集中在一座小土山上,准备进行抵抗。我们吃过午饭,用两门重迫击炮轰击,骑兵跟着往上冲锋,嘎达梅林的大太太被炮弹打死,他们连尸体都没顾上携带,即仓皇退去。我们继续追了七八十里,天已经昏黑,我叫手下最能打仗的胡宝山(跟过巴布扎布。巴布扎布,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阜新县人。民国初年聚众为匪,响应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称帝,窜扰东北,与日本特务勾结,参与“宗社党”活动,后在攻打林西的战斗中阵亡,所部溃败)连长,在野滩上笼起好几十堆野火,其余三个团的兵吃干粮和歇马。我知道嘎达梅林白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绝不肯善罢甘休,黑夜一定前来摸营,故布了这种疑阵。果不出我所料,后半夜他们突然冲来,胡宝山的兵在火堆附近打,隐蔽的兵从外边包围,打死了一二百人,其余的人各自逃命,图为以后互不掩护,到了天亮以后,大都沿途四散,我们一直追了二百多里。嘎达梅林只带了四五十人,朝南面败退,连那个叫牡丹的二太太,也被扔到一个牧民家里。胡宝山走进去见他的脸部和我们一样冻得铁青。经过恐吓,她说了实话,便被胡宝山带上做了老婆。后来我投降日本担任了伪蒙古军总司令,胡宝山跟着我升了团长,牡丹给胡宝山在呼和浩特生了一个男孩。胡宝山在宝昌死后,她下落不明。
我带领着部队紧追嘎达梅林残存的四五十人,始终没让他走脱。他们进入农业区,被民团打得无法进村,只好忍着饥寒落荒而走。我的一千多骑兵队他们越围越紧,最后把他们味道达尔罕旗舍伯吐北的洪格尔敖包的老哈河边。因为我的马快,带着十几个卫士跑到河边把他们卡住,令队伍往上兜捕。其时正是开河时期,老哈河里流着冰排,嘎达梅林一看冲不出去,便骑马泅水过河。我下了马和我的张副官爬在一个土塄上,叫士兵给装子弹。我俩用步枪一替一枪地向这四五十个人射击,一共打死了二十多个,泅水上岸的二十多个。打死的有八具尸体被马拖上对岸,其余的均被冰排冲走。我看见泅过河的二十多个人聚到一起突然折回,知道一定是嘎达梅林还没有安全泅过,他们冒死前来接应。我的兵也有十几个骑马跑进河里,有一个被冰排冲走,其余都泅到对岸,还有不少的兵也要泅过去,均被我制止。接着泅过河的兵和原在河北岸的兵一齐向这二十多个人开枪,他们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似乎在等待省么。我在河南吆喝着过了河的士兵,将八具尸体上的人头完全割下,用刺刀挑了起来,这二十多个人才向东南退去。
因为有十几个兵搁在河那边,我很不放心,我叫他们带上人头和大队隔岸顺河而走。走到有渡口的地方,找了两只渡船,放下去也被冰块打碎,后来走到河宽水浅的地方,因为天已黄昏,决定第二天由此处全军泅水而过。我便带着大队和过了河的十几个兵在河谷的冷风中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从这个水浅的地方一起安全渡过。经过达尔罕旗的一个部队的住处,哈丰阿的父亲滕海山在那里当队长。他代表该旗的王爷给我们准备下肉面,叫我们在那里吃饭。我在东巨勒克川捉住嘎达梅林的一个小兵,原来是滕海山的差人。因为回去探家,被嘎达梅林的人裹到里边。他怕我带到开鲁枪毙,看见滕海山就哭。我把这个小兵交给滕海山。这个小兵告诉我,八颗人头里有一颗镶金牙的,便是嘎达梅林。滕海山过去认了一认,也说是嘎达的脑袋。我以前把嘎达令的人当成是“蒙匪”,所以死命追缴。听见滕海山说是反对王公的起义部队,感到非常后悔。
我把人头带回开鲁交给崔兴武。崔兴武认为奇货可居,用木匣装起交给汤玉麟,汤送到沈阳交给张学良,张交给达尔罕王爷,在旗下悬挂了好长时期。我们那个军队,打仗时捡来的东西归谁,士兵们共捡了三百多支枪和四千多匹马。
嘎达梅林,蒙名老嘎达,是哲里木盟达尔罕王旗(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带兵梅林,汉名孟青山,所以又称为孟梅林。他因反对出放蒙地,惹本旗王爷恼怒,将他关在土牢里,准备捏造罪状,把他处死。嘎达有两个老婆,二的名叫牡丹,会使手枪。她联络的四五名亲属,打开徒劳将丈夫救出。从此嘎达被王爷逼上梁山,便组织了许多牧民,展开武装斗争,震动了整个科尔沁部和辽宁热和边境。由于牧民缺乏革命经验和战斗装备,必须联合马贼(旧中国时东北的蒙族土匪)来对付王府的“小队”(旧中国时东部蒙旗衙门或札萨克的武装),难免有不少坏分子被吸收进去,将牧民奇异的性质变成流寇式的活动。嘎达无法制止,最后被我智慧的东北骑兵第十七旅全部消灭。
此事发生于何年何月,我已记不清准确时间。战争的结束,则记得是一九三零年农历二月二十四。那时张学良已经继承他的父亲张作霖通知了东北四省。他和热和政府主席汤玉麟部站在王爷一边。所以嘎达起义后,辽宁拍张海鹏部骑兵有洮南向西追击,热河电告开鲁的第十七旅崔兴武部到鲁北从东防堵,以期把嘎达的部队包围解决。我那时任崔兴武部三十四团团长。这一年冰雪很大,崔旅长养尊处优,不肯亲自出动;四十一团团长孙寿卿在开鲁装病,根本没有随军前往;二十七团团长孙凤阁,到了鲁北也躲在烧锅房(酒坊)图舒服去了。因为我好大喜功,这三个团骑兵共一千多人,全归我带领指挥。我那一团人是由马贼和胡匪组成的。嘎达梅林遇见我这个对头,不仅全军在热河的扎鲁特旗遭到覆没,连他本人也被我亲手击毙在北老哈河里。
嘎达梅林的队伍共有七百多人。他们因为被张海鹏压迫的不能在科尔沁部存留,企图沿着草地畔子,在热河北部大小巴林旗的坝前整休。坝后下了四五尺深的大学,察哈尔省乌珠穆沁旗的牧民赶着牲畜和车辆在坝前之气帐幕放牧。乌珠穆沁的牧民相当富有,携带着大量的白面、炒米。嘎达梅林计划利用这一部分给养,在哪里度过严寒的动机。张海鹏部,粮饷非常充足,官兵都不愿意吃苦受罪,将嘎达梅林的部队赶到达尔罕旗的草地即停止前进。崔兴武部是有热河游击马队编成,是东北军中的游杂队伍。官兵都想利用打仗发财,所以越省进入达尔罕旗北部。我从鲁北出发时,判断嘎达梅林必然要采用民国初年的“蒙匪”战术。在他们被张海鹏部赶到草地畔子被我堵住以后,即紧紧“焊上”跟着不放松一布,形成他们做熟饭,我们赶上去端碗,使他们没有喘息的余地。否则,他们空室清野,我们找不到食物,便会越追越远。
达尔罕旗和热河东北部的几个蒙旗,地形越往北越宽广,越往南越狭窄。由于北面的牧区人烟稀少,牧民听见嘎达梅林的部队过来,恐怕抓人赶马,都以“联庄”(各村联合)的形式开出民团戒备。因此嘎达梅林的队伍只好在中间的半农半牧区,南北有四五十里的空间地带自东向西流动。在一个名叫土列毛都的村子附近,我们把嘎达梅林的队伍截住,经学堂地(村名)和东西巨勒克(村名)往西直追。一白天追越了五个旗的境界。追到林东北面以后,我感觉这样追不是办法,因为他们能赶牧民的马群,骑累了可以更换,所以跑得更快,这样他们必然会走脱。同时我知道乌珠穆沁有七八百“小队”,在大小巴林旗的坝底下保护牲畜,决不让嘎达梅林的部队过去就食,一定要进行抵抗。我不分昼夜追赶三天,官兵都把手指冻坏,腹部全部冻成铁青,很难在追到大坝底下,同乌珠穆沁的“小队”夹击他们。于是决定转进土列毛都,以逸待劳,等他们从坝底碰壁回来再在这个地方将他们一网打尽。
嘎达梅林被我追了几天,以为我一直在他们后边跟着。当他们在龙头山北乌珠穆沁的“小队”顶住,不得不由西向东折返。因为来时的路上已经抢掠一空,又怕碰见我的队伍,于是朝北沿着牧区的边缘退却。嘎达梅林的队伍走到土列毛都附近,郁郁周围再没有村庄,两条路在这里归到一起,必须进村休息。我撤至土列毛都,对外进行了严密封锁,所以嘎达梅林不知道我们驻在这里,冒然走进我的埋伏圈内。当时正是半晌前的时候,我暸见一片黄尘底下来了一千多穿着汉族妇女红绿衣裳的“乌合之众”,以扇面队形向土列毛都跑来。走到临近,我朝天打了一排手枪子弹,士兵全上马追击,一口气冲了七十多里,在东巨勒克川把他们打散。除沿途被击毙的俘虏二三百人外,一些徒手的被东巨勒克川的农牧民用铁锹劈死。马匹东西被我们掳获,士兵们捡“洋捞”捡得忘了寒冷。
中午,嘎达梅林利用我们打尖的时候,把剩下的二三百人都集中在一座小土山上,准备进行抵抗。我们吃过午饭,用两门重迫击炮轰击,骑兵跟着往上冲锋,嘎达梅林的大太太被炮弹打死,他们连尸体都没顾上携带,即仓皇退去。我们继续追了七八十里,天已经昏黑,我叫手下最能打仗的胡宝山(跟过巴布扎布。巴布扎布,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阜新县人。民国初年聚众为匪,响应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称帝,窜扰东北,与日本特务勾结,参与“宗社党”活动,后在攻打林西的战斗中阵亡,所部溃败)连长,在野滩上笼起好几十堆野火,其余三个团的兵吃干粮和歇马。我知道嘎达梅林白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绝不肯善罢甘休,黑夜一定前来摸营,故布了这种疑阵。果不出我所料,后半夜他们突然冲来,胡宝山的兵在火堆附近打,隐蔽的兵从外边包围,打死了一二百人,其余的人各自逃命,图为以后互不掩护,到了天亮以后,大都沿途四散,我们一直追了二百多里。嘎达梅林只带了四五十人,朝南面败退,连那个叫牡丹的二太太,也被扔到一个牧民家里。胡宝山走进去见他的脸部和我们一样冻得铁青。经过恐吓,她说了实话,便被胡宝山带上做了老婆。后来我投降日本担任了伪蒙古军总司令,胡宝山跟着我升了团长,牡丹给胡宝山在呼和浩特生了一个男孩。胡宝山在宝昌死后,她下落不明。
我带领着部队紧追嘎达梅林残存的四五十人,始终没让他走脱。他们进入农业区,被民团打得无法进村,只好忍着饥寒落荒而走。我的一千多骑兵队他们越围越紧,最后把他们味道达尔罕旗舍伯吐北的洪格尔敖包的老哈河边。因为我的马快,带着十几个卫士跑到河边把他们卡住,令队伍往上兜捕。其时正是开河时期,老哈河里流着冰排,嘎达梅林一看冲不出去,便骑马泅水过河。我下了马和我的张副官爬在一个土塄上,叫士兵给装子弹。我俩用步枪一替一枪地向这四五十个人射击,一共打死了二十多个,泅水上岸的二十多个。打死的有八具尸体被马拖上对岸,其余的均被冰排冲走。我看见泅过河的二十多个人聚到一起突然折回,知道一定是嘎达梅林还没有安全泅过,他们冒死前来接应。我的兵也有十几个骑马跑进河里,有一个被冰排冲走,其余都泅到对岸,还有不少的兵也要泅过去,均被我制止。接着泅过河的兵和原在河北岸的兵一齐向这二十多个人开枪,他们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似乎在等待省么。我在河南吆喝着过了河的士兵,将八具尸体上的人头完全割下,用刺刀挑了起来,这二十多个人才向东南退去。
因为有十几个兵搁在河那边,我很不放心,我叫他们带上人头和大队隔岸顺河而走。走到有渡口的地方,找了两只渡船,放下去也被冰块打碎,后来走到河宽水浅的地方,因为天已黄昏,决定第二天由此处全军泅水而过。我便带着大队和过了河的十几个兵在河谷的冷风中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从这个水浅的地方一起安全渡过。经过达尔罕旗的一个部队的住处,哈丰阿的父亲滕海山在那里当队长。他代表该旗的王爷给我们准备下肉面,叫我们在那里吃饭。我在东巨勒克川捉住嘎达梅林的一个小兵,原来是滕海山的差人。因为回去探家,被嘎达梅林的人裹到里边。他怕我带到开鲁枪毙,看见滕海山就哭。我把这个小兵交给滕海山。这个小兵告诉我,八颗人头里有一颗镶金牙的,便是嘎达梅林。滕海山过去认了一认,也说是嘎达的脑袋。我以前把嘎达令的人当成是“蒙匪”,所以死命追缴。听见滕海山说是反对王公的起义部队,感到非常后悔。
我把人头带回开鲁交给崔兴武。崔兴武认为奇货可居,用木匣装起交给汤玉麟,汤送到沈阳交给张学良,张交给达尔罕王爷,在旗下悬挂了好长时期。我们那个军队,打仗时捡来的东西归谁,士兵们共捡了三百多支枪和四千多匹马。
订阅:
博文
(
Atom
)